“科幻电影,凑热闹不如打基础”
本篇文章5752字,读完约14分钟
2019年被称为“国产科幻电影元年”。 但是自《流浪地球》以来,科幻电影没有新的佳作。
今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快速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SF10条”,极大地推动了科幻电影的快速发展。 “科幻热”的背后,存在着市场供需矛盾,也是专家极度缺乏的原因。 面对科幻电影,中文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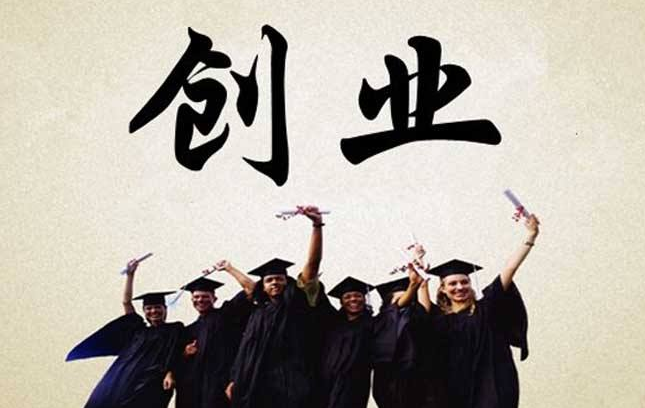
王红卫
资深电影导演、编剧、策划。 1991年至1995年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199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 1999年至2007年分别去德国、美国留学。 2006年至年担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主任。
策划剧本的主要作品有电影《疯狂的石头》《无人区》《心中的迷宫》《暴裂无声》《被光暴走的人》《疯狂的外星人》《流浪地球》等。
这是王红卫第二年参加蓝星科幻电影周。 国内很少有以科幻为主题的电影节展览,每次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在论坛上,主持人让“金牌计划”的王红卫讲话,最近的科幻项目的观后感怎么样了? 他说:“科幻小说太热了,项目特别多,不够审查。 我们几个人总是这样,看起来很厌烦。”
观众发出笑声,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结束考核工作,还没来得及参加颁奖仪式,王红卫就急忙赶高铁回北京,还有很多事件在等着他。
傍晚,经过南京牛头山下的星巴克时,他特意点了一杯拿铁咖啡,“醒一醒”,立刻埋头做手机工作。 预计这种忙碌的状态还会持续很久,只有春节才能休息几天。
疫情并未消灭人们对科幻小说的热情。 作为《流转的地球》的策划、编剧,这一年王红卫收到了多个科幻剧本。 但是,“很多质量令人担忧”。
用科幻电影的眼光来看,没有达到科幻的基准线。 如果不是科幻小说,光从普通电影的眼睛来看,似乎一夜回到了15年前。
那是2005年,中国的电影市场才刚刚开始,观众再次走进电影院,所有人都很高兴。
在大学导演系任教的王红卫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享受闲暇的时间了。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他开始忙碌起来。 很多剧本和项目送到了他手里。 那个时候,他的看法有点不是项目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连基本的戏剧常识都没有。

经过15年的快速发展,电影项目的常识性错误越来越少。 直到这两年,突然变热的科幻电影,似乎让他回到了15年前。
一切都让人担心。
科幻电影绝不仅仅是太空、人工智能等几个已有的类型
解放周末: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蓝星科幻电影周,创投项目的质量比一年前进步了吗?
王红卫:比起我之前看到的剧本,以及平时接触的社会项目,确实有一些进步。 这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希望继续“配合”科幻电影的原因。
解放周末:但是也指出了一些犯了常识性错误的剧本。 这些剧本是来自没有经验的“外行”,还是职业编剧可以操纵其他类型的电影,科幻却不行?
王红卫:前者很多,第一是大量外行涌入。 因为去年《逆转的地球》火了,让很多人看到了科幻这个类别,产生了很大的话题量和影响。 有些人认为科幻是风投,是机会。
有些人本来就是科幻爱好者,到现在为止没有电影相关的工作经验,可能只是写小说,看电影。 突然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大屏幕上很流行,所以试着转行看电影剧本吧。
也就是说,专业编剧写科幻是最起码的,他们可能不会犯戏剧常识性的错误,但是科幻的核心不足,大多数只是穿着科幻的外套。
这三种人,比例大致是4:4:2。
解放周末:这次创投项目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 例如,有一个从自行车墓地展开的故事的核心。 因为对外太空的憧憬,有连接青春的怀旧和中年危机的项目。
王红卫:总体来说,可以说是“多元化”。 这次看到的项目,不全是硬科幻,有些人想要拓宽科幻主题素材的边界。 从不规范的定义来说,有“心理科幻”、“数学科幻”、“语言科幻”等林林总总。
科幻电影绝不仅仅是太空、人工智能等几个已有的类型。 我非常鼓励中国电影从本土社会文化出发尝试科幻。 中国科幻热兴起后,应该有更大的空间。 让年轻人尝试更多的新东西。
解放周末:但是,舆论似乎很关注“硬科幻”。 人们认为,拍摄成功的硬科幻电影,意味着我们的科学技术、文化、工业体系达到了一定的综合水平。 越来越多的寓意和期待,其实就在电影之外。
王红卫:就硬科幻主题素材而言,我们目前的人才储备、工业储备严重不足,无法支撑好几个部分。 可能找不到《逆转的地球》以外的第二成熟的队伍。
另外,我不喜欢用“弯道超车”这个词灌鸡汤或者画大蛋糕。 但是,无论生产者还是观众,都迎来了科幻电影时代的到来,如果适合这一代年轻电影人的创新,也值得鼓励。
制作几部成功的电影比说一万个词有用
解放周末:近两年来,谈论科幻电影、谈论技术的文案增加了。 例如“虚拟工作室摄影”、“后期前置”等。 因为《流转的地球》的成功刺激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成长?
王红卫:工业体系涉及意识水平、技术水平、制度水平、管理水平等多个方面。 一般来说,科幻类型的电影对工业系统的刺激很大。 这是因为科幻大片有非常多复杂的流程、分工和团队合作,无法由导演一个人的力量完成。
《流转的地球》的剧情减半后,概念设计、特效创作等都介入了进来。 剧本全部结束后,我想我会再一步一步来,直到现在还没有上映。 它成功了,开始认识到电影具有工业属性,大制作类型的电影需要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制作流程逐渐受到业界的重视。 这是对电影产业体系的良好促进。

例如,我国特效企业more vfx在《流转的地球》之前制作过大量的电影特效。 但是,即使把前面很多东西加在一起,也没有“流转的地球”那么有名,所以企业以这种速度而闻名。 不再轻视中国的特效工业,我意识到特效不再是“打补丁”的工作。

解放周末:郭帆队、宁浩队的核心人才,听说电影完成后,散落在中国各类电影的创作中。
王红卫:这些人像种子。
工业体系如何建立? 除了钱,政府不能制定。 既不能由专家呼吁,也不能由学者设计。 第一,整个领域需要有工业意识。 第二,需要有能力的人,踏踏实实在所有岗位工作,系统才能逐渐成长。
给予一定的时间和空之间,等待种子发芽。 这些人的散居,最终将对电影产业体系的成长和完整性起到重要作用。
解放周末:有人总结说好莱坞电影是制片人中心制,我们是导演中心制。 对于科幻电影来说,哪个制度比较好?
王红卫:这个话题很有趣。
卢卡斯是好莱坞现代科幻电影产业的创始人,他独创地导演了科幻作品,后来成为了出品者。 他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也是以制片人为中心制。 我和郭帆开过玩笑,你以后也当卢卡斯吧。
电影独创性的时候,主创团队往往身兼数职,导演、电影制作合一。 领域之门打开后,主流科幻电影可能朝着制片人的中心制快速发展比较好。 由于科幻电影所需的工业体量太大,导演难以依靠个人力量完成,制片人需要在各个环节进行流程的封闭、策划、资源的调整等。

现在,在我们领域,在好莱坞拥有长时间经验的回国人才很少。 几年前可能有,但他们水土不服就走了。 现在活着的、活跃的人才,都是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有些人会杀蜜蜂,追逐潮流,追求“宏大的史诗”,但做比说更重要。 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制作一些成功的电影,比说一万个词有用。 只有做了很多事情,才能知道那是什么,才能谈论更迅速的发展和研究。
解放周末:怎么能说是“成功的电影”?
王红卫:我觉得自己做的是一部好作品。 不是来自他人的评价,也不是来自票房的表现。 我不太在意外界的声音。 如果是好作品的话,票房也会卖出去。 那就是饭后甜点。 肚子是否饱,首先要看自己的心情。
看着《流转的地球》最后变成一片的瞬间,我心里觉得差不多好了。 即使最后卖得不怎么好,我也对我们队很满意。
解放周末:类似的项目还想继续挑战吗?
王红卫:我一定会想的。 喜欢玩的人,一定喜欢新的东西,想打破记录,寻求新的刺激。
“青葱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这些“野生”的幼苗
解放周末:电影产业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教育问题。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你会将近年来科幻电影的快速发展文案纳入课堂教学吗?
王红卫:基本上我参加的电影,上课一句话也没说。
解放周末:为什么?
王红卫:我是老师,并不是作为业内人士去学校分享实践经验。
个人认为所有电影的成功经验都是个案,但都只是这部电影的成功。 艺术创作行业没有复制的可能性,一件事变成一件事。 老师教的最重要的是“基本真理”,特别是基础性的,不是案例。
解放周末: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用于领域怎么办?
王红卫:和毕业真正成为导演,一定相隔了很多年。 这几年需要自己磨练。 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机构。 老师教你基础的意识和技术,毕业后能做什么,在领域里担当什么样的角色,都需要你自己继续成长。
解放周末:这个时代的学生和上世纪90年代有电影梦想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王红卫:有了变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现实了。 20世纪80年代,上电影学院的机会很难得,录取率很低,大家都特别珍惜,想克服各种困难,努力。 可以说入行成功率很高。
现在有些孩子文化成绩上不了大学,推测可以去中戏,北影也很风光,所以报了电影学院,说起来好像不比大学差。 这些孩子可能并不是真的喜欢艺术,而是带有功利、方便的想法。 当然,也有有梦想的孩子。
我经历过“70后”、“80后”、“90后”、“00后”的4代学生,从整体上看,感觉在创作的天分和克服困难的毅力等方面,世代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这是时代的不同吧。
解放周末:你还担任了支持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的“青葱计划”理事长。 对培育优秀的幼苗似乎还有热情吗?
王红卫:十年来,我参与社会活动、创作活动时,确实发现了许多“野生”的幼苗。
其中有些人高中没毕业,有些人不是电影艺术,有些人是婚庆出身,没有受过顶级专科学校的训练,但他们的天分、热情、意志力可能整体上优于大学学生。 虽然他们只能来我们导演系的对外公开课,但是这些“蹭课生”的表现往往很棒。 说实话,我想帮助这些“野生”的幼苗。

另一方面,技术门槛越来越低,电影产业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 供需矛盾,“野生”苗机会增加,更容易被我们看到。 “青葱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他们。
解放周末:评价导演或主创是否成功,或电影项目是否成功。 有标准或规则吗?
王红卫:依靠直觉,直觉其实是一段模糊的经历吧。 所谓的标准和法则,我可以想“白呼”的很多词,但是落到字面上,总觉得好像有偏差。 艺术行业的事,不太容易定量描绘和用语言表达。 经验和直觉很重要。
科幻电影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梦想,是世界万物想象力的释放
解放周末:你最近打算把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科幻电影上吗?
王红卫:我没有想得那么深刻。 有事就做某事。
虽然在科幻电影中只是类型,但它已经得到了得天独厚的优待。 这几年有科幻电影节、电影周、电影论坛,几个月前,国家提出并大力支持《SF10条》。 但是,现在没有主流的例如悬疑电影节、动作电影节等。 这是科幻电影的幸运

解放周末: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小受影响,有机会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科幻作品,在其熏陶下,对科幻产生了亲近,确立了审美理念和观影标准。 作为“65后”,你是如何对科幻主题素材感兴趣的?
王红卫:多亏了家里的藏书,在上小学之前,姐姐有凡尔纳的小说。 这包括“海底两万里”等。 也有一点科普书。 是我的科幻启蒙。 所以是少数从小就接触过科幻小说的“老人”。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珊瑚岛的死光》等科幻电影的第一个高潮。 现在很火的美国科幻电视剧《西部世界》改编自1973年的《西部世界》和1976年的续集《未来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未来世界》作为优秀的翻译电影被引入上映。 我小时候有幸在电影院看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包括之后的《星球大战》系列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拨号热已经过去了。 随着长大,科幻事件逐渐被遗忘。 现在中国商业电影崛起后,科幻电影出现了很大的可能性,小时候埋下的种子觉醒了。
解放周末:所以说中国未来的科幻大作创作者一定是“80后”以后的年轻人。
王红卫:对。 必须是从小看科幻长大的一代。 科幻作品大多数时候都是少年时代的迷恋,长大后能更有成就。 美国和欧洲一代科幻大师基本上都遵循这个规律。 好莱坞最初的科幻高峰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科幻概念几乎都能从这些作品中找到母题。 世界著名的科幻电影导演,可以看到当时是青少年时代,其中某种代际规律。

在中国,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如果没有从小的相遇和熏陶,很难拍摄出科幻的艺术感。 当然可能有例子。 但是,总体来说,未来的中国科幻导演,都是来自“80后”和更年轻的一代。
解放周末:现在,电影界的“80后”导演崭露头角了吗?
王红卫:虽然已经是中产阶级的支柱了,但是拍科幻电影的很少。 不仅仅是导演的错,第一可能缺乏好的剧本和项目。
解放周末:现在的网络小说为电影界提供了许多剧本的雏形。 科幻电影有没有考虑过从中大浪淘沙?
王红卫:全世界的科幻电影都有创作规律:原创多,改编少。 一般来说,现实的主题素材、个人传记、社会主题素材等多是从小说改编的例子。 在非现实主题的素材电影中,原创剧本不断增加。 从法则上讲,科幻小说还需要原创。

解放周末:有科幻片观众,科幻片持续快速发展。 近年来,年轻人对幻想主题素材的接受度和趣味性越来越大。 类型电影兴衰的背后也与社会的迅速发展、时代背景有关吗?
王红卫: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古今中外,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志怪传说、诗词歌赋大多寄托着浪漫的幻想。 纵观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多个神话传说、寓言故事。 从较长的时间轴来看,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虚构幻想的比例可能更高。

解放周末:有人说这是人类基因的本质。
王红卫:可以想象不存在的东西,也可以描绘从未见过的东西。 大脑的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毫无根据的想象力是人类这一物种特有的天赋,不应该被压抑。 电影的魔力是将大脑通过空想象的世界在所有人面前最大化。

科幻电影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梦想,是世界万物想象力的释放,因为这可以获得更大生命意义上的共鸣。 在各方面,想象力都没有远亲,我们的未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标题:“科幻电影,凑热闹不如打基础”
地址:http://www.qdgzw.com/kjcy/40987.html
免责声明:京青年创业网是一个专业为创业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创业资讯媒体,更新的资讯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京青年创业网编辑将予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