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电影的求新变”
本篇文章4875字,读完约12分钟
被改编成真人电影的二战主题电影《血战钢锯岭》()的剧照
连日来,有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电影的话题持续上升为舆论热门排行榜。 本文力求改变70年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电影的新图,一目了然地说明了漫长而又弥新的飞速发展历史。
20世纪前的50年是电影作为新兴的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高度迅速发展的时代。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动荡不安,国家纷争不断,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东西冷战和军备竞赛。 人类对战争悲剧的恐惧和担忧并没有随着两次大战的远离而消失,而是反战、反核以及以此为中心的世界和平愿景,成为了20世纪后半叶到现在世界的主流价值观。 无形中,这一背景赋予了战争主题电影巨大的快速发展空,使之成为人类表达、宣泄战争焦虑的文化载体,使战争电影成为20世纪世界电影最重要的常规类型之一。

从广义上看,反法西斯电影可以分为军事主题素材和非军事主题素材两种。 军事主题素材一般以战场军队、军人和其他武装人员为主角,直接表现爱国者和侵略者、正义和非正义的军事对抗和冲突。 例如《沙漠之狐》( 1951 )、《最长的一天》( 1962 )等; 非军事主题的战争电影,一般旨在再现战争环境下的非军事人员、平民生活的境遇和感情的变化。 最有名的例子是意大利电影大师罗伯特·罗利尼的三首战争歌曲《罗马,毫无防备的城市》( 1945 )、《战火》( 1946 )、《德国零年》( 1948 )、《卡萨布兰卡》( 1942 )、《生死朗诵》

残酷战争的现实是电影艺术,就像往水里扔石头一样,必须掀起涟漪。 现实中的石头越多,分量就越重,水中引起的涟漪也就越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电影的历史轨迹,也像水中的涟漪一样,变小变大,逐渐扩散,派生出品种复杂、种类丰富、主题丰富的电影宝库,为现代世界电影山峦叠嶂、高耸入云。

跨越“重装”和类型的界限,不断更新战争电影的类型定义和影像范式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战争片成为好莱坞主流商业类型之一。 20世纪下半叶至今,各国电影人通过对战争素材的广泛挖掘和深入诠释,不断改变注意和捕捉的视角,在不断提高的电影技术的推动下,在世界市场高唱凯歌,为《老虎》做出了贡献! 老虎! 老虎! 》( 1970年)、《拯救大兵瑞恩》( 1998年)、《珍珠港》( 2001年)、《硫磺岛来信》()、《敦刻尔克》()、《决战中岛》。 俄罗斯的《解放》( 1971 )、《围城》( 1975 )、《莫斯科保卫战》( 1985 )、《斯大林格勒》()和日本的《战争与人》系列( 1970-1973 )、《中国的百团大 这些电影史经典不断更新战争电影的类型定义和影像范式,在叙事结构和视听语言方面,越来越趋向于被称为“大体量”、“全景式”和“叙事化”的美学维度。 场景仿佛不大,结构多而庞杂,视野不开阔,情感不炽烈,收视效果不震撼,就不足以再现战争场景的艰巨性,雄浑宏大。 这个方向在现代战争电影中塑造了“重装化”的新趋势。

人物传记片也是表现战争的常见类型之一。 例如,众所周知的《伯顿将军》( 1970年)、《国王的演讲》()、《模仿游戏》()、《极黑暗的时刻》()等。 以前,人物传记电影为了描写战争的重要作用和领导人的人物,刻意强调英雄史观。 把他们独特的个性、非凡的意志、超人的智慧、以及内心辗转的挣扎,表现为惊人的心理奇观,让观众产生了高山仰止的敬仰和崇敬之念。 近年来,随着电影故事妙招的提高,人物性格的形成越来越多地趋向混合化和精巧化,抛弃了过去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表现方法,英雄回归世俗人性。 个性依然张扬,情智二商依然与众不同,但更让观众喜欢,显然他们身上是你我一样的七情六欲,甚至比你我更胆小、焦虑、犹豫和恐惧。 但是,悬念绝对能在故事结束前展现出英雄和懦夫真正的不同,英雄最终总能战胜焦虑拯救自己,而懦夫只会继续沉沦。 所以,有人说现代英雄塑造靠的是“逆转”而不是“高大”。

另一种受欢迎的战争电影类型是战争喜剧。 卓别林的《独裁者》( 1940年)、刘别谦的《你逃离我也好》( 1942年)法国的《虎口逃出》( 1966年)、《王中王》( 1982年)、在此影响下诞生的国产喜剧《三毛从军记》 从常识上讲,战争意味着悲伤、痛苦和不安,喜剧似乎没有界限。 喜剧往往需要支撑战争的黑色和厚重,跨越悲伤和创伤的强大正能量。 因为这部喜剧被认为是强者、胜者的艺术。 只有摆脱悲伤的泥沼,生命才能大步向前。

喜剧与战争电影的对接是类型的跨界融合。 也许是现代战争电影经久不衰、持续繁荣的秘诀。 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创伤正在愈合,心灵的疼痛也在减轻。 战争片跨越其他电影类型的国界融合,成为当今世界电影寻求创新突破的最佳亮点。 在那里,我看了战争电影、奇幻、童话融合的《面包神的迷宫》( 2006年)。 与儿童电影融合的“穿着条纹睡衣的男孩”( 2008年); 与儿童电影、喜剧电影融合的“乔乔的异想世界”( 2019年)。 此外,还有战争片与惊悚、恐怖、甚至无厘头等体裁混搭融合的《死亡之雪》系列( 2009-)、《弗兰肯斯坦兵团》()和最近的《战争幽灵》()等吸引指数火爆的怪塔 也有人把电影现有的文化积累比作圆。 今天的电影人应该做的就是将它的边界向外扩展,为电影制作寻求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类型的跨界融合是驱动电影边界扩大的引擎。

摆脱类型模式,强调电影艺术的个性化和创作思维的多样化
好莱坞电影遵循的是类似福特汽车流水线的集约化模式。 这总是为客户提供完美固定的费用途径,为电车铺好轨道,提供市场脱轨不可逆转的潜在风险。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这条路还擅长暗合被称为“圣经故事”的史诗原型,将任何战争中的敌我双方转化为正与恶的终极对立。 或者把正义一方的主角变成从恶魔手中拯救苍生的创世英雄。 集合型是为了简化思考,使之容易成本化。 但是,长期以来,封套本身也发展成为创作上刻板印象、思维束缚、束缚、阻挡电影人拓边创新的艺术尝试。 因此,跳跃类型模式,强调电影艺术的个性化和创作思维的多样化,成为当代世界反法西斯电影谋求新图变化的另一个法门。 电影大师大卫·琳的《桂河大桥》( 1957年)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电影也取材于二战的史实,但主题中大师一贯关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美学意义仍在继续。 它不仅使电影获得了文化反思的价值观,而且在其风格上留下了作者电影特有的“签名”式的个人印记。

在20世纪1950~80年代,这种“去类型化”和“作者化”的趋势在国际电影界日益明显,如《士兵之歌》( 1959 )、《伊凡的童年》( 1962 )、《铁皮鼓》( 1979 )、《雷曼》( 1981 ) 近年来广为人知的“无耻混蛋”( 2009 )、“沉默的迷宫”( )、“金衣女”( )就是沿着这种“类型化”、“作者化”方向的延长线。 《沉默的迷宫》和《金衣女》都是欧美有识之士面对二战和排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 前者呼吁现代德国社会要勇敢地打破记忆,面对悲惨的历史,自己承担战争遗留下来的司法和道义责任。 后者包含着“不能忘记,但是应该放下仇恨”的实务史观,帮助在战争中受害的人们从痛苦的记忆中获得心灵的痊愈。 这样的电影不仅为现代人类社会提供了文明的尺度,而且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警告着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未来、和谐共处的挑战。 它们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电影艺术和美学本身的框框,应该被视为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但是,市场很严峻。 正如无论多美味的食物都要面对顾客味蕾的检验一样,它们在文化思想的艺术价值上各有所切的艺术成果,但有时也要面对顾客无法接受的不自然的情况。 毕竟,大规模的战争远离了我们,战争的创伤也加速了愈合。 当今主流人群,特别是最常去电影院的年轻一代,对如何看待战争的态度普遍表现出麻木和迟钝。 这一客观现实要求电影运营商必须从电影的美学机制中重新寻求应对措施。 在那里,我们又看到了被称为“隔代物语”的剧本的带入方法。 例如,日本电影《永远的零》()和《小房子》(也译作《东京小屋》)不约而同地起用了当时正当的红流量明星作为历史故事的倒退者。 他们在故事的主线上,不承担性格展开的故事功能,只是作为一个外在故事中、与观众同龄的讲述者,将遥远而陌生的战争传说带入当今年轻一代观众的视线,最大限度地缓冲戏剧与观众之间的陌生感。 应该说这样的变革是必要的。 因为它涉及到“念念不忘”的文化祭祀,有助于年轻一代更有效地汲取失散的宝贵记忆。

推进视听语言的感知革命,成为大屏幕的坚定捍卫者
年初,人类社会和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之间爆发了毫无预兆的遇难战。 电影产业受到严重破坏,电影院停止上映。 由于无法进入电影院,蜂拥至流媒体网站,舆论中对于是否可以代替以前播出的电影院上映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如电影院复工后带来的观影热潮所示,当人们将观察力转向“云观影”等新兴观影模式时,也不能忽视之前流传到电影院的流媒体竞争的应对措施。 外卖更适合小食,而餐厅更适合正餐。 “在线看电影”和“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新旧之间必然会出现不同电影种类的选择和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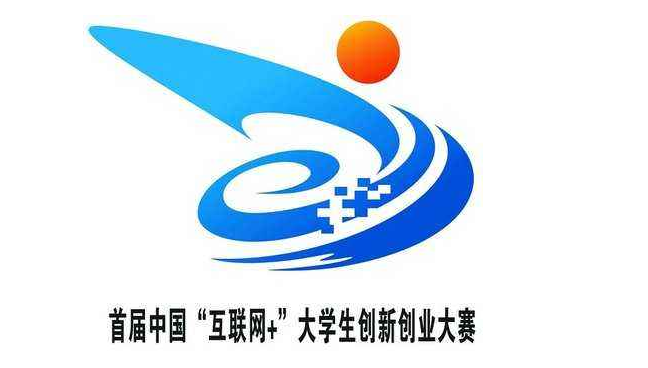
对于战争电影来说,越来越强大的电影院的观看效果显然可以提供比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屏幕更合适的放映效果和电影环境。 年,杜比公司推出了128声道影院全景音响( atoms )系统,在放映馆为观众提供前、后、左、右三维沉浸式音响。 《血战钢锯岭》是率先利用杜比全景音响系统营造真实战场气氛的电影之一。 当观众放下身影厅,感受到掠过自己身后、头顶的枪炮轰鸣,血脉喷张,就会意识到这种上映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级感受,是以前传到电影院碾压屏幕的真正魅力。

电影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带来战争电影创作上的美学变化。 前几天上映的一战电影《1917》( 2019 ),是数字后期模拟的《一镜底》,为观众设置了假设场的视线,让他们跟随剧中的两个小兵,逐渐穿越前沿阵地,深入敌阵,扮演角色。 比起以前流传的着重故事魅力和性格的电影,这部电影的《一镜到底》更明显的侧重于为观众创造真实的“沉浸式”体验。 你可能不太在意发掘人物多而复杂的性格深度。 另外,我可能不太重视戏剧结构的精巧程度。 其目的是将观众深深推入戏剧的“现场”,让他们无间隙地分享角色和生死一线的战地气氛。 它直接诉诸观众的感觉体验,不像以前流传下来的电影那样致力于对观众理性和思辨的诱惑和觉醒。 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体验力电影”,将其视为流媒体时代大银幕电影自我救赎的“感知革命”。

这场革命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二战主题素材《敦刻尔克》()等电影的背后也悄然发生。 李安之所以冒巨大的商业风险,是想以120fps的高帧率和4k、3d技术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也是根据他的话,让观众从银幕外的观众变成故事的直接参与者一样,采取观影的态度。 观众和屏幕之间没有“我”和“他”的距离,之前流传着电影“主观”和“客观”的边界,在高度真实的视听效果和感觉体验中遁形。 《敦刻尔克》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也表明了与李安相似的美学尝试。 为了这个伟大的实验,他抛弃了以前流传在电影里的才构建起来的成熟叙事经验,不再向观众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解释角色的经过,对白也压缩成了极其简洁的几句话。 诺兰手里,以前电影的线性故事流传下来的时候空的结构,就像被孩子们撕裂后再次堆积起来的积木一样。 他在不同的时候空彼此重叠,交叉情节,使镜头的视线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 其目的是让屏幕外的观众摆脱21世纪的观影环境,重返20世纪40年代的战火。

有人可能会抱怨诺兰的电影太受欢迎了,但他的态度很明确,让我们给《权力游戏》和《纸牌屋》这个故事看长剧,统治电视和流媒体吧。 把电影院和巨幕留给“纯粹的电影”。 根据我们的理解,诺兰的意思是,正如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一样,包括反法西斯电影在内的战争电影也由于电影技术的进步,以其自身独特的影像语言和视听魅力,成为以前在电影院流传的坚强捍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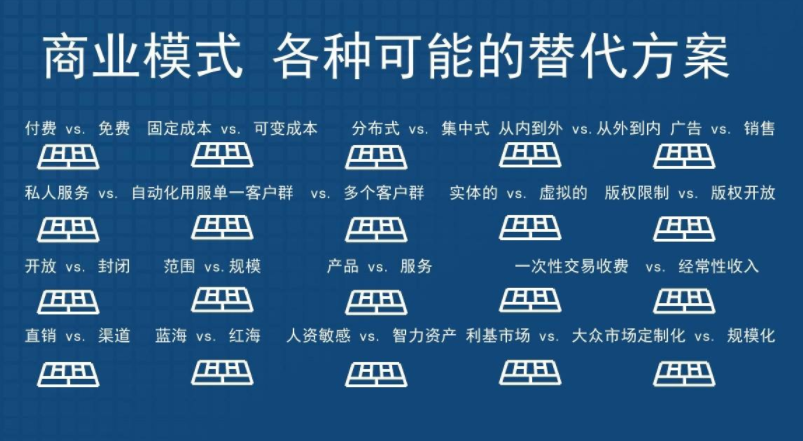
(作者石川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标题:“世界反法西斯电影的求新变”
地址:http://www.qdgzw.com/kjcy/41122.html
免责声明:京青年创业网是一个专业为创业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创业资讯媒体,更新的资讯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京青年创业网编辑将予以删除。
上一篇:“《匿名者》将在电影频道播放”
下一篇:“野孩子 哪些固执唱歌的中年人”

